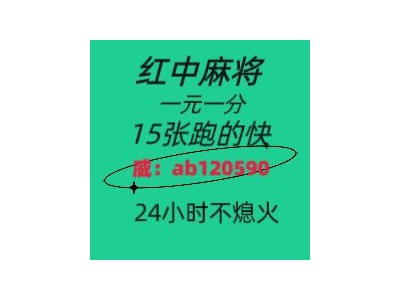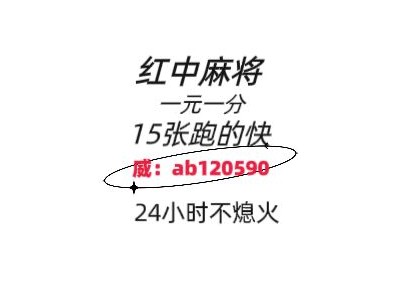二〇一七年终,晓航公布了短篇新作《捉飞贼》(《群众文艺》第十二期)
在这篇演义里,飞贼能否生存明显比“捉”的进程更要害,作者由此想商量的是他从来此后试图经过文艺表白所实行的:在都会宏大而搀杂的框架里那种无穷的大概性以及新颖性和后新颖性的辩论
“我想在演义里创作一个悬殊于庸常体味的寰球
”在晓航可见,这明显比大略弹性地表露外部实际更要害更有价格也更有欢乐
恋爱需要一个幽静的处所,而在树下往往是最佳的选择
在树下切切私语或轻轻嗔怨;在树下泪沾衣衫或山盟海誓;在树下相抱相依或挥手离别……总之在树下恋爱会让恋爱者变得更加本色起来,让双方各自透视对方的真诚度
无论恋爱成功与否,多年后,一提起或不期而遇某一棵与你关联的树,你会真切地感到自己曾年轻过曾爱过曾追求过
想想吧,在日益缺少树木为有情人遮蔽和作证的年代,爱情会不会掺假或变味呢?
一日闲坐赏画,想到自己刮诗的事,蓦地想到,唐伯虎作画、乾隆题诗、我刮诗,三个时代,一条流淌不息的时光之河
时光是多么公正啊,而它又那么喜欢调侃:一些东西想凭一时得势把渺小变成伟大,把丑陋变成美丽,到头来必定会还原真面目,历史和后人,自有公论,也自有办法
一寺为云光寺,它比起外地的寺来讲,其规模也太小了
但据传此寺存有明代的御赦万岁牌匾
正应了这么一句话,寺不在大,有佛则灵
这天是街天
人头晃动的街上,碰上了专程来接我的朋友及山寨中一大帮赶街的哈尼人